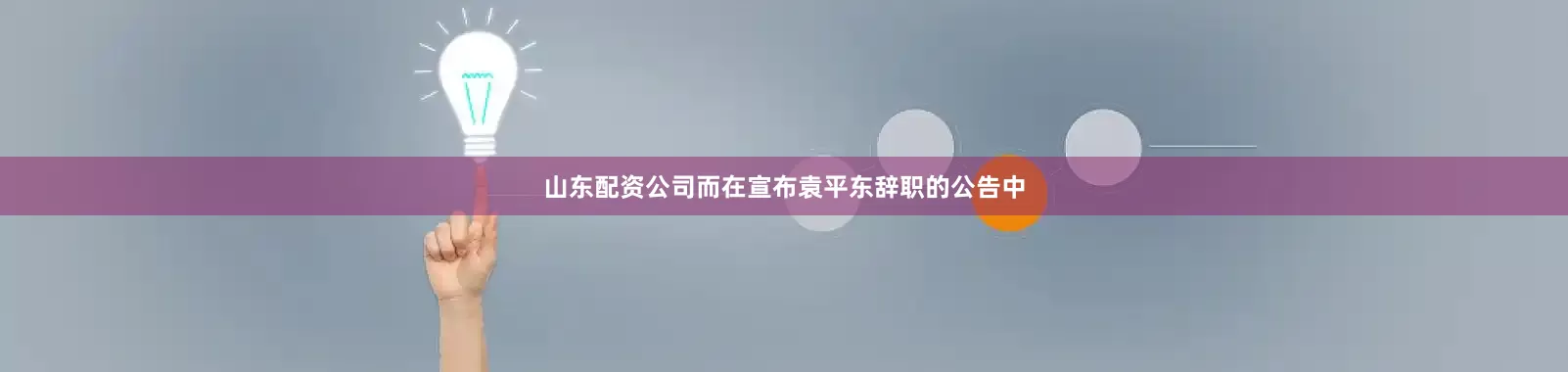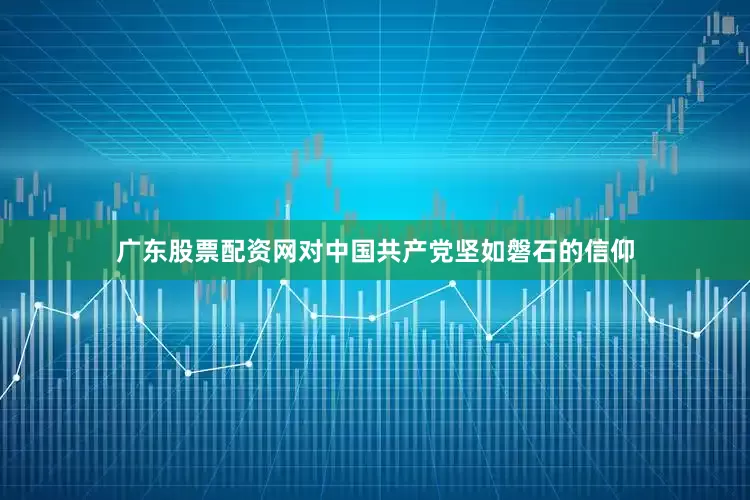冯梦龙是否是作家,是否是伟大的作家,这首先取决于他是否创作了能影响时代并流传后世的优秀作品。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代表其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三言》中就有不少作品,例如故事发生在苏州地区的几篇小说,是他的原创或原创性作品。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只把冯梦龙认定为资料、故事的搜集、汇编者,充其量只肯定他在整理改编这些资料、故事中的贡献,很少有人肯定他是一个作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多人认为冯梦龙不是原创作家。
其实,这是对冯梦龙的极大曲解。
但曲解冯梦龙观点的产生,又是首先依据冯梦龙编纂《三言》时写的“序”及出版时写的“广告语”。换句话讲,曲解冯梦龙观点的源头是冯梦龙本人提供的。
这个悖论如不破解,辨析判断将难以进行。
我们确实看到,在冯梦龙出版《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时,以“绿天馆主人”署名的“序”中明确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昇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冯梦龙不用真名,而布下两个迷阵——“绿天馆主人”和“茂苑野史氏”,其实这都是冯梦龙用的为使他人不能知道本人真实身份的笔名。
明朝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的“封面识语”还说:“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更把“三言”的一百二十篇小说均列为“搜集、汇编”之列。在《警世通言》中,冯梦龙又布下两个迷阵:以“豫章无碍居士”为笔名写“序”,“序”中又称该书系“陇西君”所刻。
在明朝三桂堂刊本《警世通言》的“封面识语”还说:“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再加上一个迷阵。在《醒世恒言》中则以“陇西可一居士”为笔名写“序”。

冯梦龙布下迷阵的底线是告诉读者:这些小说并不是自己创作的,而只是从“家藏古今通俗小说”中,“抽其可以嘉惠耳者”,汇编出版的;用现在的话说,他充其量(即使在被人发现真名后不得不承认时)也只是“搜集”“汇编”者。
从而进一步掩盖了他亲自改编乃至创作某些小说的真相!这样,即使有人查出《三言》确是冯梦龙出版的,但也不能认定是他的原创;换句话说,也就是事先表明《三言》不代表本人的真正立场。用心可谓良苦!
冯梦龙为什么有意向读者传达以上错误的信息呢?首先我们要对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所处环境有所了解。当时,“科举取士”为正道,“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们的处世原则和策略。
冯梦龙很早考中秀才,后来却一直未能中举,他恨主考官有眼无珠,也看到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病,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否定或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

在他屡屡落第、生活无着的情况下,为了生计(当然也寄寓他的愤懑和追求,但这也是不能明言的),他不得不编纂出版“三言”等畅销书,却羞于公开自己的身份。为此,不得不布下重重迷阵。
即使到了晚年,冯梦龙已从寿宁知县的任上退隐回乡,《三言》又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冯梦龙也仅仅十分谨慎地透露自己“向作《老门生》”(即《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于是后人长期认为《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中仅能认定《老门生三世报恩》一文为冯氏作品。这是当年那个时代造成的畸形现象,不能由此苛责冯梦龙!
当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三言》出版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于是引发了冯梦龙好友凌蒙初(他也是才学渊博,而又长期科举未中)的创作灵感,他开始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创作与出版活动。
此时由于《三言》的巨大成功,凌蒙初认为不必再为冯梦龙作太多的掩饰了,于是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称:“……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按,这八个字着重说明《三言》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无根本决突),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
我们知道,“龙子犹”是冯梦龙为当时世人知晓的名字,常用于文学和戏曲作品,与故意隐匿自己而用的“茂苑野史”等笔名不同;当然,它与冯梦龙出版儒学研究作品时直接署名“冯梦龙”又有不同。
不管怎样,凌濛初在这里首次披露了《三言》系冯梦龙所“辑”的事实。但凌濛初尊重冯梦龙的底线意见,仍沿用《三言》的说法,称“宋元旧种”被冯氏“搜括殆尽”,也就是仅仅说冯梦龙是搜集汇编者。

与冯梦龙不同的是,凌濛初(当然,他的前提是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比较大胆袒露自己创作《拍案惊奇》的艺术手法。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应“肆中人”之请,“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
“演而畅之”即创作之义也。后人仅仅看到这些,又产生了曲解,认为凌蒙初的《拍案惊奇》系创作,而冯梦龙的《三言》反而只是汇编。
实际上,凌蒙初也并不愿意彻底“埋没”冯梦龙的艺术创作贡献。故过了若干年后到崇祯十二年,冯梦龙与凌蒙初合作选编并出版《今古奇观》时,其原书内封页题有“墨憨斋手定”字样,说明选编者确为冯梦龙(按,这个观点见于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1版,我很赞同)。
其时冯梦龙已从福建寿宁知县任上退休回苏州,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而此时凌濛初正式出任徐州通判,无暇兼顾编书出版此类杂务)。这时冯梦龙用出了“墨憨斋”这个常用笔名,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使用掩饰身份的笔名。

既是冯、凌两人作品的合集,由凌濛初写“序”当在情理之中。此时凌蒙初因在官位上,故用的是“姑苏笑花主人”的笔名写“序”,没有出示自己的真实身份;提到“《拍案惊奇》”,也仅说是“即空观主人”所作,也不说是个人创作。
而对其时已退休在家的冯梦龙(墨憨斋),则说得较直白:“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按,已充分肯定冯梦龙增补《三遂平妖传》中的创造性劳动)。至所纂(注意,不是以前说的‘辑’)《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观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抜新,洞心诫国。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已成为对“三言”的经典性评论,应当也是对冯梦龙“纂”写“三言”的高度评价。
但凌濛初对冯梦龙“三言”评价提法从“辑”到“纂”的巨大变化,却似乎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人(包括本人在内)对“纂”的内涵作具体分析。
现在是揭开历史真面目的时候了!学术界多年来对“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素材来源的详尽考究,已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材料,关键是采用何种方法加以认定!
对冯梦龙作品的发现和研究有个很长的过程,很多人做出了贡献。我在1984年撰写《试论冯梦龙及‘三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福建论坛》1986年2期采用时改题目为《“三言”为文学史提供了哪些新东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立即于1986年第5期在《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中全文转载,更为权威的《新华文摘》也于1986年第7期作了摘载)时,根据当时考据的成果,认定冯梦龙编纂(请注意,我用的是编纂二字,既不是编,也不是纂)了“三言”,并进行了总体分析和评价。

到1989年,我根据当时考据的新成果,并针对不少人只把冯梦龙认定为资料、故事的搜集、汇编者,从而对冯梦龙艺术创作贡献估计不足的情况,又写了《从“情史”到“三言”》,并在1991年苏州召开的中国俗文学学会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该文首次具体论述冯梦龙编纂“三言”时进行再创作的四个层次的贡献:一是“移花接木”,进行部分改编;二是丰富情节,充实作品内容;三是根本改动,提高了思想性;四是根据现实生活,直接进行创作。
在当时许多史料尚未得到挖掘的历史背景下,我仅作出这样的判断:“虽然目前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能说明系冯梦龙创作的小说仅《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有数篇反映明代生活,却又找不到出处的小说,极可能是冯梦龙根据现实传闻编写的。”我举了“杨八老越国奇逢”和“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为例,并做了简单的说明。

后来我逐步发现,该文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没有充分反映冯梦龙直接根据生活进行创作(而不仅是收集或简单改编宋元旧作)的实际成就。
最近我重新汇总研究多年来学术界考据的成果,做出了以下新的判断:冯梦龙编纂“三言”时,当然也有不少作品是取自宋元旧作。
但至少有几十篇作品,主要源于他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没有任何旧本依据,完全是冯梦龙根据生活创作的。第二类是有原始出处;但冯梦龙作了根本性的改动,尤其在根据现实生活塑造人物方面有重大突破。
以上两类均属于冯梦龙本人原创或原创性作品,应当据此肯定他的艺术创新贡献。从而确证,冯梦龙无愧于伟大作家的称号。
要具体论证几十篇作品的来龙去脉,非一两篇文章所能完成。本文且以《三言》中故事发生在苏州地区的几篇小说为例,具体论述这些属于冯梦龙本人原创或原创性作品的根据。我在此提出了以“排除法”为主的认定方法。
先讲第一类,即没有任何旧本依据,完全是冯梦龙根据生活创作的作品。
例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明朝事,发生在吴江县。故事出处仅见于冯梦龙《情史类略》卷二“情缘类”(岳麓书社《情史类略》第51页)中的“吴江钱生条”,时间标明为“万历年间”,地点明确为“吴江县之‘下乡’和‘洞庭西山’”。
《情史》中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该故事的最早来源和出处,仅注明“小说有错占凤凰俦”。我觉得,“情史”“吴江钱生条”应是冯梦龙以文言文的形式,把他创作的小说《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主要内容压缩改写而成。

因为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在此之前的任何笔记或史料中,写有类似的传闻。《情史》又注“沈伯明为作传奇”;经查沈伯明的传奇写在“三言”之后,该传奇应该也是根据“三言”小说《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改编的。所以可以断定,该小说是冯梦龙独立创作的作品。
例二,《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明嘉靖事,发生在吴江县盛泽镇。
与该小说有关的资料仅见于冯梦龙编《古今谭概》卷36“张生失金”条(引自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古今谭概》第1167页)。
“张生失金”条全文如下:“嘉靖时,杭人张姓者,自幼为小商,老而积金四锭,各束以红线藏于枕。忽夜梦四人白衣红束,前致辞日,‘吾等随子父,今别子去江头韩谦家。’觉而疑之,索于枕,金亡矣。踌躇叹息。之江头询韩,果得之。张告韩曰‘君曾获金四锭乎?’韩惊曰:‘君何明知? ’张具道故。韩欣然出金示张,命分其半。张固辞谢,遂出门。韩留觞之,举一锭分为四,各裹并中,临行赐之。张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济以饼一。四乞者计曰:‘此饼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韩易小而热者乎?遂之韩,韩笑而易之。’”
这个故事被写进《施润泽滩阙遇友》,成为小说的一个细节;但与主人公施润泽一生的故事比较,该细节是极微不足道的。

此外,我们至今找不到本篇故事主要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重要细节从何处来。这只能反证,该小说是冯梦龙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积累而创作的。
与此同类型的,还有《张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明万历事,发生在苏州市区“ 门外宝华亭”;《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15,明朝事,发生在昆山县。此二篇均至今未见任何出处,应当是冯梦龙的原创作品。
概括来说,以上四篇属第一种类型,即至今找不到小说的任何出处,反证它们是冯梦龙的原创作品(当然还要分析原作全文,确证它们反映的是苏州明代生活)。以上方法,我称之为“排除法”,是否准确,请大家讨论!
第二类作品,经研究找到了冯梦龙小说依据的原始出处;但对照后发现,冯梦龙已作了根本性的改动,尤其在人物塑造方面有重大突破。对这种冯梦龙作了根本性改动的改编作品,我们应当肯定他的艺术创新的贡献,并列入原创性作品。
例一,《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醒世通言》,明正德事,发生在昆山县。这是有原始出处的。冯梦龙《情史类略》“情贞类”卷一“金三妻”条(岳麓书社《情史类略》第11页)写出故事梗概,并注明引自王同轨《耳谭》一书。
可以说,《耳谭》中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具备了。但从人物的塑造角度来说,则十分平淡,毫无特色,更看不到性格的发展变化。
冯梦龙在小说《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根据生活作了详细铺写和重大改编,完全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

他把主人公由金三改为“宋小官”,把宋小官设计为家庭逐日衰败的书生后代(其一是父死,其二是母不善经营。在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苏州,是十分典型的)。
宋小官在家景败落后被昆山舟师杨姓者收留,经过艰苦的改造,才逐步转变为能自食其力,且懂得人情世故的小商贩。有了这样的转变条件,后来他因病被岳父抛弃荒岛后,才能采取变被动为主动的冒险举动,转变就有了合理的依据。
可以说,冯梦龙通过小说这种艺术手段,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一个由世家没落子弟转为暴富商人的真实形象。
基于这样的理念,小说结尾也作了重要变动。《耳谭》原记:“会剧冠刘六,刘七叛入吴。三出金帛幕死士,从郡别驾胡公,直捣狼山之穴,缚其渠魁,讨平之,功授武骑尉,妻亦从封云。”
金三在《耳谭》中依然是个坚守仕途的封建人士。而冯梦龙小说的最后安排是, 宋小官夫妻发迹后,回到昆山故乡扫墓,追荐亡亲,家族亲戚各有厚赠。此时原先刻薄过宋小官的范知县已罢官在家,闻知宋小官发迹还乡,恐怕街坊撞见没趣,躲向乡里有月余不敢入城,可见当时苏州社会风气发生了从“重文重官”到“同时重商”的巨大变化。

小说结局是:“宋金定了故乡之事,重回南京,阖家欢喜,安享富贵——子孙为南京世富之家,亦有发科举者”。宋小官成为商人世家的小说结尾,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金三妻”这个故事,当时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古今闺媛逸事》卷四《情爱类·破毡隐语》也转载了《耳谭》的记录。《古今情海》卷十七《金三妻》条亦引自《耳谭》,文字完全相同。冯梦龙《情史》卷三“金三妻”条亦注“事载《耳谭》”,文字略有出入。
说明《耳谭》确为原始出处,其对冯梦龙创作灵感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冯梦龙也是十分尊重这个事实的!但我们更要看到,冯梦龙通过自己的艺术再创造,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新商人形象,则是《耳谭》原载故事远远不能企及的。
例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小说中把故事放在“大宋景祐年间”的“杭州府”。
细读原作却是写苏州的生活。经多人考据,查其原始素材出于南宋《醉翁谈录》丙集卷之一“因兄姐得成夫妇”。原故事发生在“广州”,主角是“以机杼为业”的手工业者“姚三郎家”。以弟代姐出嫁后出现鸳鸯错配,最后以私了结束,皆大欢喜。
这个故事应当说是很有意思的,但情节比较简单,尤其是缺乏有个性特征的人物描写。也许冯梦龙当时没有读过这则材料,所以在《古今谭概》和《情史类略》中都没有提到《醉翁谈录》。
现有的材料说明,冯梦龙《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创作灵感应当更多来自生活,尤其是他长期居住的苏州地区。

他在《古今谭概》卷三十六中,以“嫁娶奇合”为条目,记录了自己听到的生活传闻:“嘉靖间,昆山民为男聘妇,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说,遣媒议娶。女家度婿且死,不从。强之,乃饰其少子为女,归焉,将以为旬日计。既草率成礼,男父母谓男病不当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寝,而二人竞私为夫妇矣。(按,‘冲喜’之不良风俗是前因,错配的双方虽有错,但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逾月,男疾渐瘳,女家恐事败,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无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穷问得之,讼之官。狱连年不解。有叶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妇得婿,颠之倒之,左右一义。遂为夫妇焉。”(按,叶御史的司法调解还是比较明智的。)
冯梦龙又在《情史》卷2以“崑山民”为条目,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只是在条目的最后作了明确的说明,“小说载此事。病者为刘璞,其姐已许字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孙氏,其弟孙润亦已聘徐雅之女。而润以少俊,代姐冲喜,遂与刘妹有私。及经官,官乃使孙、刘为配,而以孙所聘徐氏偿裴。事更奇,其判牒云(略)……)。”(该判牒与冯梦龙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理念一致)

这里又提供了一个例子,证明《情史》卷2条目“崑山民”是冯梦龙把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压缩为文言文写成的。
同时,冯梦龙还有意无意地向读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他根据生活传闻编写的,结果是“事更奇”,即情节更为曲折、丰富、复杂,更为吸引读者。但他没有明确点明,自己在人物塑造上作了新突破。
其实人物塑造的突破性进展,才是冯梦龙的最大贡献。如见官之后,少女刘慧娘表现了空前坚决和勇敢。于是那个“又正直、又聪明、怜才爱民、断案如神,被称为乔青天”的关西人乔太守才做出了判决。
判词中体现了全新的理念:“爱女爱子,情在理中”“相悦为婚,礼以义起”。这判词完全是冯梦龙起草的,他人写不出来,体现了冯梦龙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也是小说中最动人之处。

《2016福建冯梦龙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王凌、林松涛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冯梦龙的这类改编(不是编辑意义上的小改动,也不是一般性的改编)体现了巨大的创造性艺术劳动,包含了原创内涵,应列入原创性作品,与上述第一类共同构成冯梦龙作品的精粹!
嘉喜配资-嘉喜配资官网-投资股票配资-网上配资开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